責任主編:王顥中
一部關於漢娜鄂蘭──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的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在台灣上映了。雖然無法排除其他國家的片商也曾受到更平庸的片名翻譯所誘惑,但畢竟是台灣發明了這個副標題;而無論考慮影片本身的內容,或影片所描述的歷史段落本身,「真理無懼」四個字,就算不是可笑的偏差,至少也是某種相當冷僻的幽默。
在我看來,《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書寫以及其後的吵嚷,幾乎與真理的追尋毫無關係。而作品本身也不完全是哲學探索的結晶。就如鄂蘭自己在本書再版中一開頭就提到,接著又幾次暗示的,這並不是嚴謹的歷史或哲學作品,只能算是一篇報導文字;在台灣的語境裡,或許也只能被稱為特稿或報導文學。
而作者在全書中只提到少數幾次的「Banality of Evil」,惡的平庸性,更是成為後世眾多知識份子引用或爭論的焦點。在中文世界,除了同樣的浮泛操作之外,更被開了個怪異的玩笑,導致於出現「平庸之惡」或「平庸的邪惡」這類,很可能只為了語音通順就予以句型倒裝的翻譯。若直接針對這個詞彙在書中,乃至於鄂蘭學術生涯中的比重,或許還不算是太嚴重的誤譯;但如果考慮到它被拿來作為理論性概念去理解、溝通,甚至作為一套理論在其上辯駁的歷史,這個倒裝的嚴重性,可能不下於一個打字錯誤讓菠菜的鐵質含量高了十倍,結果讓菠菜在一時之間人人搶購,至今仍被當成補充鐵質重要來源的科學界公案。
然而,儘管近代研究已經修正了關於菠菜的誤解,社會的慣性與現象的複雜度,依舊讓這類公案成為茶餘飯後的笑談,讓我們可以輕易地用「菠菜對人體還是有很多好處」之類的修辭,維持自己與普遍認知的共感(菠菜是最富有鐵質的食物範例),或者將共同行動合理化(同意購買菠菜以求補充鐵質的效果)。論述效果的事後修正,對於改變因其擴散而形塑的社會現象並無太大作用;而光是去理解這類事實的重要性,儘管結果可能只是一個相對合理的校正,卻常常因此被荒謬地被正面扭曲為對真相的堅持、或負面扭曲為無聊的鑽牛角尖。
這當然並非毫無意義。從發生在19世紀的菠菜公案之中,我們不但可以窺見統計數字的力量,更可以由此探伸出某種,當代藉由散佈謬誤或誇大訊息作為公關手段的雛形。而從鄂蘭一生汲汲於解析的對象,以及又重新開始圍繞她發展的那些,被扭曲得奇形怪狀的論述,乃至於這些論述的政治根源與政治效果,很容易就能讓人看出這個以悲劇來攪混鬧劇的當代論述結構。
台灣社會使用文字時,在細究與粗放之間的拿捏,顯得因人因事而異。這畢竟是一個只要提到「內地」兩字就會激起複雜而激烈情感的所在;對同一塊地方稱呼「中國」與「大陸」的人群彼此可能並不相容,「中國大陸」也似乎不被接受為折衷或合併的方案。「愛台灣」被某些人認為單純是某種意識型態的產物;「大中國」則彷彿是另一些人被激怒後用以回擊的概稱。另一方面,從漫畫借用的「天龍人」概念遍地浮現,因為指涉範圍的可能性太多而難以定義,卻又讓每個人都能隨時道出自己堅信的意涵,同時在彼此定義並不相同的前提下產生共識;更驚人的,譬如許多人似乎認為只需要「鬼子」、「支那」、「神棍」、「政客」、「黑道」之類的詞彙一出口,就可以滿足對某個政治事件的發言需求。
語詞本身會引起情緒,並自動激發一連串符號連結的現象,特別是在公共領域裡,多數都是緣於意識型態的作用。但是意識形態在公共場域運作的形式,卻並非自我揭露,而多半是事先隱瞞自身的框架,同時由操作者揀選自認足可引起共鳴的元素,再加以傳播。我們對民主精神最基本的認識裡,公開以可供檢驗的理念或邏輯彼此交流,進而決定集體事務的概念,因此便少了一些能讓彼此全盤檢驗的透明度;而對意識形態作用的不察,包括無法識別論述背後意識型態的存在、無法考慮意識型態隱藏部分在公共論述裡的作用、無法理解操作者進行隱藏或凸顯某些文字的操作理由、無法意識到種種操作如何直接影響公共領域的決策或個人領域的思考方向等等,都將使個人在無意間成為意識型態操作的俘虜,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成為操作者直屬的下線,不直接卻又主動地協助達成那些操作的目標。
是什麼讓我們忽略了這些意識形態的作用?是什麼讓人抱持著堅定的理念,遵循意識型態機器所提供的一切指引,執行這種意識型態不存在時便不會有,甚至不願意去做的行動?以及,是什麼讓人認同這些行為能協助完成意識型態的終極任務:一個更好的未來、一場撥亂反正的革新,或一次集體攻克的成就?在這裡,鄂蘭透過《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寫作問得更深:是什麼讓人能夠一面認定自己正在積極地恪遵社會賦予的道德價值,同時卻又能與這個社會聯手犯下抹滅人性的罪行?
而她的詮釋也走得更深。在〈思考與道德思量:一段講綱──致 W.H. 奧登〉一文中,她在提到「惡的平庸性」的說法時認為,行惡之人甚至連「意識型態的信念」都可能付之闕如。
但如此一來,我們又該怎麼理解鄂蘭在《艾》書中強調的,艾克曼並非毫無目的、毫無中心價值的行政機器;而是如他自己陳述的,一個希望自己能作為未來世代的表率,並且將自己的所有努力都視為「理念者」的行動,不止忠實地遵循長官命令,甚至在大戰情勢將定,所有納粹官員都急著變現求存時,還違抗同一個長官停止行動的命命,堅定跟隨自己的所謂榮譽與良心,決意將實為屠殺的「最終解決方案」執行到最後一刻?他所跟隨的榮譽與良心,他所認為國家賦予他的任務,他所能理解的元首敕令與法制科層機器,難道不是透過意識型態的構作方式,才得以組織,並深入整個世代的德國人心嗎?
我們已經很難追索鄂蘭在〈思〉文中使用「意識型態」這個詞彙時想表達的意思,或這個談論方式是否只表達了一種盡可能擴大提問指涉範圍的意圖。問題發展到這個程度,看來只是在單一切面上汲汲鑽營,但事實上卻關乎圍繞著惡的平庸性概念的一系列爭議:鄂蘭究竟是否認定艾克曼本人就是個遵循命令的普通人,對自己行動的結果毫無所知,或刻意忽視;鄂蘭是否過度美化了這個納粹政權的官員,或受限於歷史資料的不足,導致得出錯誤的判斷?鄂蘭是否在書寫過程裡,透過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描寫,投入了對自己所屬的猶太民族的不滿,或甚至寫出了可稱為反猶的文字?她是否過於沈醉於機巧的理論辯駁,導致文字徹底脫離現實?甚至,她是否受到所謂「支持納粹」的理論大家海德格的影響,因而在關於這段歷史的分析裡,失去一部份判斷正義的能力?
漢娜鄂蘭政治人文中心的學術部門主任Roger Berkowitz,在上文提到的電影推出之後,發表了一篇題為〈誤讀《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文章[1]。 他提及史上兩次對於這本書的誤解:其一就像電影描述的,是當時紐約知識分子們,為了爭執鄂蘭是否袒護納粹仇視猶太人而掀起一場戰火;其二是後來在知識分子間彷彿形成一種「共識」:鄂蘭因為沒有看到某些艾克曼的仇恨式發言,特別是在阿根廷避居時期由「納粹記者」Willem Sassen採訪的內容與事前受訪者的筆記,以致於寫出了一本在理論上卓有成就,卻缺乏歷史判斷準確度的書。然而根據Berkowitz所知,鄂蘭其實早已在雜誌上讀到這份專訪段落,而她對這件事情所做的筆記,認為艾克曼在其中展現出一貫地「無能思考,亦即,無能以別人的立場思考」云云,也受到後世史家如David Cesarani的迴響。而暗示鄂蘭缺乏人性、鄙視同胞甚至反猶的說法,在本書裡其實也找不到多少根據。事實上,鄂蘭透過隔空駁斥艾克曼對康德學說的理解,以及書中幾次強調,並在書最後正當化處死艾克曼的理由裡,一再說明認識、思考、判別、決定,以及不傷害同類等人性的基礎,在本案審理之中應當佔有最重要的位置。
鄂蘭並不生在我們這個時代,多數的基本語彙與概念都尚未被拆解,「作為人而思考」與「人性」等詞彙都有著相當穩固的意涵。不質疑她為何堅信人類具有如此複雜的共性,卻質疑她在寫作《艾》一書時失去同理,很可能只是依循成見的過度解讀。這或許也是上文中第二次誤解的「共識」傾向批評資料不足而非誅心的原因之一。
但無論是哪一種誤解,針對「惡的平庸性」這個概念所爭執的,多半圍繞著鄂蘭對於平庸這個詞彙的定義與用法。「平庸性」這樣的詞彙,所強調的是「某事物具有某種性質」,而不像部分中文翻譯成「平庸之惡」時,忽視了這種表意上的差別。把「惡的平庸性」說成是「平庸之惡」,就如同把「研究的有效性」說成「有效的研究」,莫說在哲學區辨上造成阻礙,其中的差別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應該被辨識出來。
在鄂蘭的論述裡,「惡的平庸性」,有一部分指的是「無能思考」,另有一部分是「積極服從」;兩者間看似存在矛盾,但若我們加入鄂蘭堅持人類應有作為判準的「人性」,那麼這兩者便可以與其他因素同時構成惡。這時可以回顧Judith Butler評論這個爭議時留下的斷定[2]:鄂蘭堅信,只有哲學思考才能結束,甚至預防像納粹屠殺那樣的災難。我們因此可以提問:難道惡的平庸性果真讓人徹底無法思考?這種平庸性果真只存在於人們為了意識形態彼此殺戮的所在,而不存在於當下,也無關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樣:主流社會總是認真且積極地服膺這種或那種價值,並且費盡心思企圖一階一階地向上爬嗎?難道我們不也像鄂蘭筆下的艾克曼那樣,崇拜著在上位的成功者們,並且傳述許多他們所謂充滿成功智慧的言語?或在所謂法治國家的僵固前提之下,甚至只在某個自己敬仰的智慧言語中,找到足以忽視其他人類處境的所有理由?就算艾克曼在法庭上所供稱的,自己與猶太人的良好交往與信任,果真都只是藉口,今天我們的社會,是否能在各種排擠或賤斥發生時,幫自己找到比艾克曼更好的藉口?甚至,是否我們需要的正是如同納粹賤斥猶太人一般,賤斥所有與納粹有關聯的人事物甚至一切符號,那怕自己根本無知於那些符號的歷史脈絡何在,以便自己活在一個足以安居而不需細緻反省的世界?而那樣的世界,能夠以任何方式預防自己再度成為艾克曼的世界嗎?
我們想起曾與鄂蘭活在同一個動盪年代的赫緒曼。後者以寫作《反動的修辭》而著名,該書常被奉為政治論述研究的經典之一,至今還時常受到政治評論者的引用。相較之下,赫緒曼的書寫更貼近我們的時代,引用時補充的說明也因此更少。他提出了「反動派」常使用的三個修辭方式:背謬論調(人類行為必然引發相反結果)、無效論調(人為改革無法造成有意義的改變)、危害論調(改革行動將危及既有成就);以及「進步派」常存有的三種態度:協同幻覺論述(所有稱為進步的行動必然協同共進)、燃眉危機論述(危險只剩一步之遙必須即刻面對處理)、終歸歷史論述(歷史終將站在我們這邊證明我們的正確)。
這些確實都是很重要的提醒,在今天,我們很難見到任何關於社會改革的正反論述,能完全脫離這些承載著論述謬誤的因素。然而這些因素並非本身就是錯誤。而像是吳乃徳在赫緒曼逝世後的介紹文章〈赫緒曼和《反動的修辭》〉[3]中所提及,後世學者批評赫緒曼並未證明這些修辭是錯誤的;這樣的批評似乎已經遠離了赫緒曼論證的原意。誠然,關於革新的正反論證,常有過度簡化與內涵缺陷等等特徵,但也只有在這些特徵存在的時候,它們本身才會成為錯誤的訊息。赫緒曼並沒有排除類似論調成為有效論述的可能性,而是希望指出歷史上這些論證方式的錯誤用途,以及它們在民主討論程序中造成阻礙的危險性。
赫緒曼的提醒儘管重要,然而,每個不同事件裡所出現個別論述的論證是否有問題,只能逐一檢視,不能概括定性。《反動的修辭》中文版譯者吳介民在〈如何破解反動的修辭?〉[4]一文中就給出了後者的錯誤示範,甚至進一步製造出「反動修辭」與「新自由主義」的連結。這看似毫無問題:新自由主義難道不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保守價值總綱嗎?然而這裡或許又關連上一個翻譯的問題。吳介民在〈如〉文後提到自己認為「反動」被賦予負面意涵相當不幸,但或許將赫緒曼所使用的「Reaction」或「Reactionary」一詞譯為「反動」,只是一個跟隨翻譯傳統的結果,並未傳達多方面的意涵。「Reactionary」的「反對變革」意涵,甚至不能直接植入所謂「保守」與「進步」的框架之間來理解;在這裡,與其翻成「反動」,不如翻成「滯動」(當然這樣就不免在另一方面破壞了編譯者想向大眾推廣的旨趣,並減損赫緒曼明快筆觸的魅力)。如果要認真對待赫緒曼的論述架構,「Reactionary」一詞頂多能說帶有「阻滯變革」的意涵。否則多半被歸為進步運動之一的苑裡反瘋車運動,便只好因為充滿反動修辭而劃歸保守陣營,甚至連提出捷運機廠防滑坡措施「無效」、迫遷老人「有害」、新院區反會降低住民生活品質的「背謬」的樂生運動恐怕都不免此禍。一個詞彙翻譯的效果,可以讓論證有著相當不同的面貌,乃至於造成一個學者的困境。而吳介民儘管受到這個困境阻擾,卻仍堅持製造反動論述等於保守的連結,是由於他心中已有明確的保守/進步圖式。這又是另一個問題,簡單地說,或許這正是為什麼「進步」力量會在具備反思能力的前提下,仍然以幾種論述穩佔赫緒曼所謂「另一個極端」的位置吧。
現在我們把上文敘事裡的幾個元素,從後向前推演一次:
- 吳介民翻譯赫緒曼時,將「The Rhetoric of Reaction」譯為「反動的修辭」,如此便忽略了作者採用詞彙的某些效果,並造成譯者自身的困境。
- 儘管作者幾次在書中告誡,甚至把對立項都明白地列給讀者;譯者在發表相關文章時,仍然做出過度的連結,把實為「滯動」的「反動」連結上他心目中的保守派:新自由主義。
- 引用赫緒曼的批評,時常做出類似的扣連,甚至可能只考慮保守派修辭,而忽略《反》書作者訴求民主對話時,認為兩邊都是某種必須警醒的「極端」。
這些詞彙使用上的問題,看起來細小,實際上使用起來,卻有影響整個論述的力量。比如說,指引讀者用赫緒曼提出的反動論調去分析某種論述,彷彿展示著這些論調可以作為保守論述的判準,卻不處理它用以判斷時會出現的不確定性;在邏輯推演下,便容易出現上文中所提的,社會運動被納入保守陣營的問題。
上面提到的兩位學者治學已經相對嚴謹,只是或許限於自身意識型態才有所偏漏。而當下與社會輿論同在的,卻是一種更等而下之的盲目。僅舉小例:譬如看國民黨開會鼓掌通過認為是威權的象徵,到了自己黨派開會鼓掌通過時才加上林林總總的條件來說明區別;譬如看到對手陣營因為總統選輸想移民、就認為是毫無風度,等到自己陣營選輸,同樣叫著不如快快移民;譬如看中國政府殺戮少數民族就認定是法西斯極權體制才會如此,卻忽視美國如何進行全球範圍的大規模暗殺行動(反之亦然);又譬如看到還沒有決定性政治立場的1985,就急著冠上公民運動甚至公民社會的稱號,但看到與自己立場不合的反對同志婚姻遊行,又羞於稱之為公民運動;或相反地,在主張婚姻必須只有一男一女時,宣揚傳統道德或宗教價值優位性,但在別人表達支持多元婚姻的理念時,又攻擊他們是拿著自己的信仰阻礙社會正常運行。在這些例子裡使用的修辭方式,幾乎已經沒有可供辨識的,所謂進步與反動陣營的差別。
而這可能才比較接近社會論述的現實,但也是從這種混沌不明的狀態出發,赫緒曼小心翼翼的整理工作才顯得有其價值。就算以《反》一書中最重要的歷史教訓之一:法國大革命為例,兩百多年來它啟發的反省成篇累牘,它當時所引發的恐怖統治以及社會動盪等效果也早已廣為人知。對其反省或批判的論述,無論如何,都不只是企圖阻礙社會變遷一種態度所能概括解釋。
如果我們試著模仿赫緒曼,提出當代回應論述裡幾個需要注意的重點,例如:
- 預防性宣言:以「我不是歧視,只是...」或「我同意你,但是...」或「我是個不懂複雜理論的笨蛋,可是...」作為前提,事先回應預料中的回擊以為防備。
- 弱勢主張:無視於自己究竟佔有哪種權力地位,套用既有話術,將自身與社會共認的弱勢族群作連結,以取得在道德上更為便利的位置。
- 蓄意偏狹:理解到現象的複雜程度乃是個人認識無法窮盡,個人視域的有限乃是必然,於是決定:與其採取擴充認識並含括陌生角度的艱苦手段,反而傾向去揀選並連結那些能夠符應個人意識型態的現象碎片。更嚴重的則會將這種刻意連結的偏差認知,視為知識上的成就。
...或考慮其他類似的歸納仿作等等。其實不管多麼貼近時代,這些對過往論述經驗研究的諸多歸納,由於觀察的對象是已經在社會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語言,我們無法預設只有進步或反動或抵抗或破壞性的陣營會使用它們;因此它們依舊不能當做直接判定論述屬於善惡好壞的獨立判準,頂多只能作為一些往後分析時用來提醒自己的要點,提醒的事項也應限於觀察論述本身是否完整,或能否作為公共溝通的有效工具。
從這裡,同樣可以見到《艾》一書所引發的批評有些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設想,那是一個從二次大戰期間開始,國家總體動員宣傳色彩仍未褪盡的時刻。戰爭狀態所生產出的絕對對立,包括如:德國─納粹─希特勒─大屠殺─反猶/猶太人─大屠殺─反抗勢力─同盟軍─美國這類連結。在宣傳體制之下,任何跟這個連結沾上一點邊的符號都會被迅速地辨識並歸納,任何需要推銷或詆毀某個符號的宣傳,也多會乘著這些既成的連結來傳播。一個更複雜而有趣的例子是,美國在大戰時期的反法西斯宣傳,以及五零年代冷戰氛圍下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肆虐之後,六零年代時竟冒出了穿著納粹黨軍服,揚起納粹十字旗,在美國各大學等場所公開演講,並接受媒體採訪的國家社會主義黨派運動。新的連結產生了:猶太人、共產黨、黑人與同性戀都被視為叛國行動的高危險群,而這種連結絕不限於只燦爛一時的歐美國社主義運動內,甚至到今天的保守政治基進勢力都還抱持著幾乎一致的連結方式。鄂蘭在當時所面對的,因此是極為複雜多樣,而彼此之間激烈對立的情勢與任意無稽的判斷,又難以接近多元主義狀態的政治視野。
我們或許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一篇顧及大量資料,並經過深刻思考的報導文字,竟會讓許多當代與後世人們絞盡腦汁想要證明其中存在缺漏或誤解。過度倚賴既有政治連結來進行表淺的政治判斷,譬如只要見到不願針對艾克曼進行人格謀殺的任何發言,都視為疑似反猶,這種行為無論採用哪種修辭,都無非是種謬誤。
其次,鄂蘭在書中確實重述了艾克曼沿襲其他戰後審判時,戰犯們自我辯護的用語:認為他的行動是服從上級命令,而艾克曼甚至進一步提出自己與猶太人友好的事實,以及企圖「協助」猶太人獲得更好待遇的行動。而他對自己在戰爭後期,儘管接到停止的命令,卻仍堅持繼續運送猶太人去集中營的辯駁,則是他所信仰的元首指令精神,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自然必須依此忽視明顯悖反的新指令。鄂蘭當然也認為艾克曼是一個失去思考能力的人,乃至於一個言語呆板,只剩下覆述政治宣傳口號能力的小丑。但這並不表示她同意上述的辯駁。毋寧說,她在報導寫作的過程中,透過呈現繁多歷史資料的方式,為我們鋪陳出關於艾克曼審判事件的歷史脈絡,作為與讀者共同討論的基礎。閱讀她的書寫,忽略這些脈絡,只挑選那些看似得以嵌入二分框架的斷片,甚至提出鄂蘭不曾宣稱過的各種說法,這是另一種謬誤。
但是,為什麼我們拒絕把鄂蘭的語言置入一種倫理框架來形成判斷呢?進一步說,難道指控鄂蘭的聲音,不正是試圖在哲學的冷酷機器裡,遵從鄂蘭的期望,嘗試去確認某種人性的價值,避免自己陷入無感的困境、甚至因此昧於承認對某些人群造成的傷害嗎?然而鄂蘭所撿選的歷史資料與她鋪陳的脈絡,甚至那些使批評者最為憤怒的文字,都企圖回應同樣的問題:無論是西歐傀儡政權的懸崖勒馬、北歐政權的積極反挫、中歐政權的顢頇怠惰、東歐政權比納粹更野蠻的清洗措施、乃至其他法西斯政權的遲疑或積極;另一方面,艾克曼所遭遇到的複雜情勢裡,他執行任務時倚仗的猶太長老委員會、猶太復國主義者進出體制之間掌握猶太人生殺大權的地位、瀰漫全歐的反猶氣氛、當代德國所代表的進步繁榮與法治科學精神、戰爭時期人類對生命價值的厭棄、總體主義對賤斥弱勢群體的正當化,以及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服務國家的榮譽感、不斷向上的成功哲學,以及堅守法治理念與體制正常運作的責任感。這所有排置在艾克曼身後,乃至於作為「惡的平庸性」判定基底的種種訊息,正是在挑戰我們是否真如自己宣稱的一般正義無敵,是否只要發言自認歷史正確就可以忽略一切更細緻的檢討。忽視這些細節是否在其他時代,乃至於自己周圍發生,而輕率地以平庸二字概括抹平所有更困難的思想工作,這又是一個重要的謬誤。
事實上,不同於一般使用「平庸之惡」概念的方式,鄂蘭並不是給了我們一個萬事通用的結論,而是開啟了不斷自省之路。
或許我們反而因此得以從其中獲得一些理解的工具:相對於一般認為「平庸之惡」是在使用個人的缺乏能動性為個人開脫,或回過頭來虛泛地指控個人最平凡的選擇如何阻礙不了評論者心中認定的惡,「惡的平庸性」這個概念,卻正是詮釋了人的能動性如何驅使個人,使他有意識地完成體制最瘋狂的妄念。鄂蘭甚至透過關於艾希曼審判的資料鋪陳,為我們刻畫出這個長期拉鋸的斑斑細節。另一方面,赫緒曼的論述研究以及後人的應用也讓我們看到,單純的形式對照,在很多時候都不足以證明現象之間的關聯性。沒有深究便擅意比較,反而可能成為產生謬誤的根源。
再者,對論述的用途錯誤與理解謬誤,本身也是個值得觀察的現象。很多時候,這個現象代表的並不完全是能力的貧弱,而是發言者如何受到他所順從的意識型態、社會教導或文化傳統等知識形構所限制,或激發出積極進取的意志,就像艾克曼讓我們見到的那樣。
人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在閱讀了每個時代的悲劇之後,我們很容易就能得出各種時代的謬誤作為結論。然而對歷史的反省,終究必須要在我們能依此理解當代謬誤時,才顯得更有意義。鄂蘭從極權主義與共和體制出發,赫緒曼以政治論述研究起始,都是為了讓我們更認真地看待自己的時代。
對我而言,誇張、錯置、偏狹,再加上對這些論述方式的容忍,是當代社會拒絕思考的重要表徵。而無論是保守或進步的我們,對這類語言樂此不疲,或據以為策略,甚至堅稱是為了某種價值的犧牲,比起敵對雙方彼此認為平庸而互稱為惡的現象,是更值得擔憂的癥兆。這些癥兆的負面影響已經慢慢浮現。原屬於進步陣營的話術可以輕易被保守價值取用,例如宗教團體利用多元主義論述來確保自己的信仰並拒絕申辯;進步價值採用不經反省的語彙,又容易癱瘓自身論述的合理性,例如上文提到的公民社會論,或企圖操作「平庸之惡」或「反動修辭」一類,原本引用便不精確的概念,浮濫地延伸套用,生產出無處不可用的通用指控規範,只剩下霸佔指控位置的功能,價值反而成為語言操作技術的附庸。必須警惕的是,遠在艾克曼成為重要角色之前的納粹發展初期,由國家廣泛吸納最新的商業宣傳、藝術創作、工會組織、科學技術人才,透過價值說服的過程,便為人類的現代計畫譜出最黑暗的章節。
這當然不能保證每種收納了當代最新技術的價值,都會演變成屠殺弱勢人民而不自覺的政權。但各種形式的壓迫仍然在我們這個時代橫行無阻;以往體現了人類文明進展的各種革新運動,如今也被迫演變為四處阻礙社會變遷的「反動」組織。這種無力化的趨勢,反而使得組織本身越來越傾向於採用信仰型態的意識動員方針。「無能以他人立場思考」以及「不問手段以堅持價值立場」的態度,漸漸成為眾人崇尚的標準。
而許多人仍然堅決將一個可供反省的概念誤讀成「平庸之惡」,以最平庸的老舊價值,指責他人因為堅守平庸導致無能阻止自己認定的惡。於是,或許正是在這樣的氛圍裡,我們終究可以期待惡的平庸性再次席捲整個社會。只是這次,既非鬧劇也非悲劇,卻是一個令人手足無措的新時代的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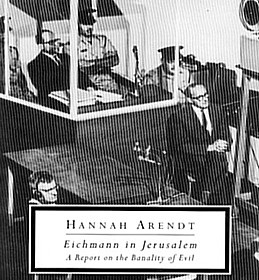 Hannah Arendt, 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Hannah Arendt, 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